民国二十三年秋,江南水乡飘着细密雨丝。青石板路上泛着油光,镇东头王记布庄的幌子在风里直打转。李秀娥坐在柜台后头,手里的绣花针在缎面上起起落落,针脚细密得像春蚕吐的丝。
"掌柜的,这匹松江布怎么卖?"布帘子一掀,进来个穿阴丹士林旗袍的妇人。李秀娥抬头刚要答话,忽听得后院传来"扑通"一声,像是瓦罐摔碎的响动。她脸色倏地白了,手里的绣绷子差点掉在地上。
"当家的?"她冲着后院喊了一嗓子,声音打着颤。自打三个月前丈夫王德顺跟着货船去上海,这后院就再没动静。起初她还当是野猫作祟,直到月前在灶房梁上发现那双黑布鞋。鞋帮上绣着并蒂莲,正是她亲手给丈夫纳的千层底。
旗袍妇人见她发愣,从银镯子里倒出两块银元:"我要三尺月白缎子。"李秀娥回过神来,正要伸手去量布,布庄木门突然"咣当"一声被人踹开。雨水泥浆溅了满地,进来个戴鸭舌帽的男人,帽檐压得低低的。
旗袍妇人见势不妙,抱着布匹溜了。李秀娥扶着柜台慢慢站起来,指甲掐进掌心:"这位大哥要扯布?"鸭舌帽忽然摘了,露出张蛤蟆脸,左眼皮耷拉着,活像被蜈蚣爬过。
"嫂子好记性。"蛤蟆脸从怀里掏出块玉佩,翡翠雕的貔貅,尾巴上缺了口,"这是王大哥抵在赌坊的信物,今儿该还钱了。"
"当家的出门前……"她话没说完,蛤蟆脸突然逼近柜台,隔着木栅栏喷着酒气:"少废话!要么拿三百大洋,要么……"他眼睛往李秀娥身上溜,旗袍领口盘着的梅花扣簌簌发抖。
忽然外头响起铜锣声,两个穿黑褂子的保丁晃过来。蛤蟆脸骂了句脏话,把玉佩往柜台上一拍:"三日后来收宅子!"说完撞开木门,泥水溅了保丁满身。
李秀娥瘫坐在太师椅上,怀里抱着丈夫留下的烟袋锅。铜锅子还温着,烟丝却早发霉了。她忽然想起昨夜做的梦,丈夫浑身湿透站在船头,身后跟着个穿红袄的女鬼。那女鬼冲她笑,嘴角咧到耳根,露出满口黑牙。

"当家的……"她把脸埋进烟袋锅,泪水浸湿了烟荷包。这荷包还是成亲时丈夫送的,湘绣的鸳鸯戏水,如今鸳鸯眼睛都褪成了灰白色。
天擦黑时,镇西头棺材铺的刘大娘来了。这老寡妇拄着蛇头拐,进门先往地上啐口唾沫:"秀娥啊,我听见蛤蟆张来过了?"李秀娥忙着沏茶,手抖得茶碗直打转。
"大娘,您说这玉佩……"
"别碰那晦气玩意儿!"刘大娘拐杖一挑,玉佩"当啷"掉进泔水桶,"这是从死人嘴里掏出来的!三年前张麻子在赌坊输红了眼,把他老娘的棺材本都押上了……"
话音未落,后院又传来响动。这次是瓦片碎裂声,夹杂着女人呜咽。李秀娥抄起擀面杖就往后院冲,刘大娘在后头直跺脚:"作孽哟!那是镇东头周家媳妇,被蛤蟆张逼得跳井了!"
雨越下越大,李秀娥踩着满地碎瓦冲进柴房。借着闪电光,瞧见梁上挂着个人,舌头伸出老长。她刚要喊,忽然被只手捂住嘴,身后传来阴恻恻的声音:"嫂子,这景致可好?"
是蛤蟆张!他不知何时摸进了后院,手里攥着根麻绳。李秀娥正要挣扎,忽听得"咔嚓"一声雷响,震得房梁直掉灰。蛤蟆张惨叫着松开手,左手腕上赫然插着根银簪子,簪头缀着的东珠还沾着血。
"当家的!"李秀娥扑向门口,却见雨幕里站着个黑影。那人戴着斗笠,蓑衣下摆滴着水,怀里抱着个湿漉漉的包裹。蛤蟆张还要扑上来,被黑影一脚踹在心窝,像破麻袋似的飞出去撞在磨盘上。
"翠花,把门闩上。"黑影掀开斗笠,露出半张烧焦的脸。李秀娥差点叫出声——这不是镇北茶馆的说书先生吗?平日里总见他在街角摆摊,讲《三国演义》讲得唾沫横飞。
说书先生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,层层打开,里头是本蓝布封皮的线装书。"这是王兄临走前托我保管的。"他翻开书页,露出夹在其中的银票,"他说若三更梆子响,必有恶客登门。"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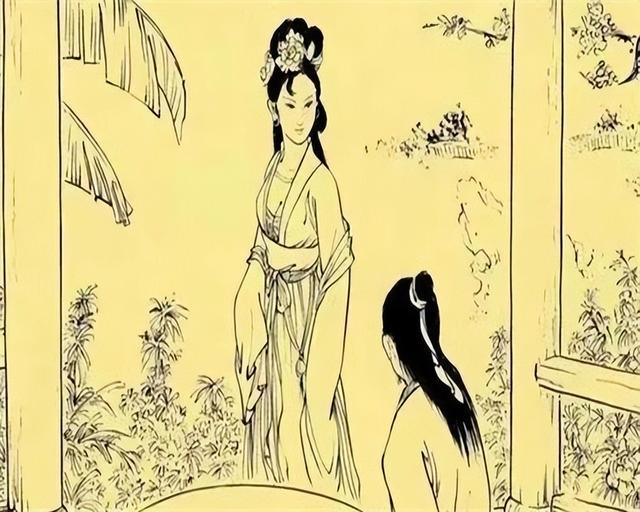
李秀娥接过银票,手抖得像风中落叶。三百块大洋,整整齐齐码在油纸里。说书先生忽然咳嗽起来,蓑衣下摆渗出暗红血迹:"快走!蛤蟆张在码头埋了二十几个兄弟……"
话没说完,外头突然火光冲天。李秀娥扒着门缝一看,整条街都烧起来了,火舌舔着布庄的幌子,黑烟里传来女人孩子的哭喊。说书先生拽着她就往后窗跑,却见墙角蹲着个红衣女鬼,正是梦里那个!
"恩公,奴家等您十八年了。"女鬼冲着说书先生拜了三拜,转身扑进火海。说书先生惨叫一声,左脸烧伤处滋滋冒烟。李秀娥这才看清,他蓑衣下藏着把驳壳枪,枪管还冒着热气。
两人跌跌撞撞跑到码头,江面上飘着几十艘火船。蛤蟆张举着火把站在船头,身后站着个穿长衫的男人,手里把玩着个青铜酒樽。"陈先生,这婆娘交给你了。"蛤蟆张狞笑着,火把映得他蛤蟆脸像恶鬼。
说书先生突然站直了身子,蓑衣"哗啦"掉在地上。李秀娥这才发现,他右腿齐根而断,装着木假肢。"陈世美!"他指着长衫男人厉喝,"十八年前你为夺《天工开物》,放火烧了王家祠堂,今日该还债了!"
长衫男人脸色大变,酒樽"当啷"落地。李秀娥突然想起丈夫的话:"咱们祖上是给皇宫造机括的,那本蓝皮书里藏着鲁班锁的秘法……"火光中,说书先生从木假肢里抽出一卷黄绢,正是《天工开物》缺失的最后一章!
"接着!"说书先生将黄绢抛给李秀娥,转身扑向陈世美。两人扭打间撞翻了火把,江面上的火船顿时炸了锅。李秀娥抱着黄绢往芦苇荡里钻,身后传来陈世美的惨叫:"我的眼睛!"
天亮时,保甲队在芦苇荡里找到了李秀娥。她怀里抱着蓝皮书和黄绢,身旁躺着说书先生的尸体——不,现在该叫他王德顺了。原来十八年前王家祠堂大火,烧死了说书先生的孪生弟弟,他便整容换面,在茶馆蛰伏多年。
"当家的……"李秀娥摸着丈夫焦黑的脸,泪水在黄绢上洇出朵朵墨梅。保丁们从陈世美尸体上搜出封信,信上盖着上海青帮的关防,原来蛤蟆张早被买通了。
三个月后,李秀娥在镇东头开了家机括作坊。她按黄绢上的记载,造出了能日行千里的木牛流马。每逢清明,总有个穿红袄的姑娘来作坊外徘徊,有人看见她对着空气说话,嘴里唤着"恩公"。

这年冬至,李秀娥关张时在门缝里发现个油纸包。里头是半块翡翠貔貅,还有张字条:"恩怨已了,珍重。"她把貔貅埋在丈夫坟前,立碑时特意刻了行小字:"身怀利器,杀心自起;心存善念,百邪不侵。"
来年开春,镇上来了个游方道士,在茶馆里说书:"话说那鲁班书分上下两卷,上卷写的是匠人巧技,下卷刻的是人心鬼蜮……"李秀娥在角落里听着,忽然抿嘴笑了。她怀里揣着本蓝皮书,书页间夹着朵风干的梅花扣。

